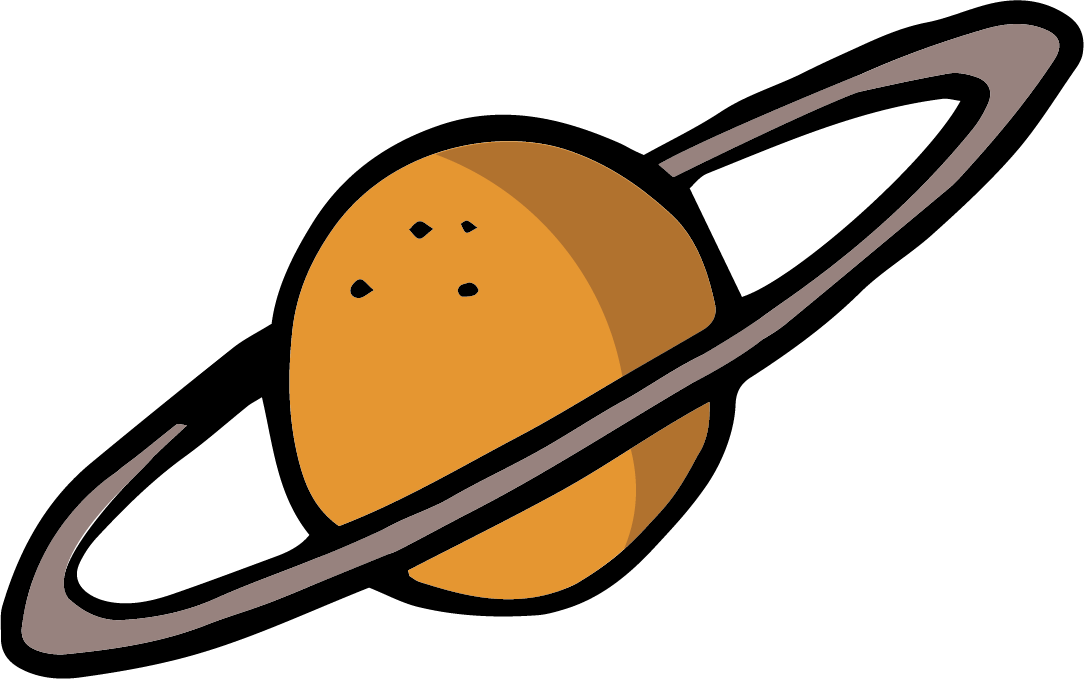三月
三月
我是在下午洗澡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是三月。
当温水顺着脖子从莲蓬头淋下来的时候,我还在老旧的世界里安稳地打转,水卡以每秒钟两分钱的速度显示在一块五毛二。
说起来我是在八年前第一次见到她的。
那个被暖气熏得头昏脑涨的午后我抱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正靠在床上打瞌睡,就是那个时候,我透过小屋仅有的窗户第一次见到了她。
那一年的三月我开始写小说,并跟朋友相约等到毕业就投给自己喜欢的杂志社。理所当然地,我也开始了故事的构思,把自己和好朋友一个不落的全写进小说里,于是便有了一个主角多达近十人的开头,整个春天都因为我的小说而兴奋而期待。
当然,夏天过了没多久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它丢在了书桌的一角再也没动过。
第二次见到她是半年后的某一天,那是个九月。
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并开始追她。那一天是周五,她穿了一身蓝色的长裙,整个下午我都无法集中精神。那天晚上我浑身冒汗,双手颤抖地发了短信给她,当我点开回信的瞬间仿佛看见了春天里发芽的柳枝,波光闪闪的小溪和明媚的阳光。
也是那个时候,因为她我再次写起了小说。
后来,就像大多数青涩而幼稚的孩子们一样,所有的事情无疾而终。
第二年的冬天,我坐在教室里花了两个中午的时间把因她而起的那篇小说改了结尾,投稿给了校刊。
再后来,毕业后的某一天我听说那篇文章连载在了校刊上,而那时的我们,人生已再无交集。
刚刚我又见到了她。
一个小时前,朋友打来电话,说他给自己放了半天假出去走走跟好朋友打打电话,于是打到了我这。
说起来我这个人我一贯擅长劝说别人,进而演化为一种虚无的犬儒主义。这一套理论在劝慰别人时尤其具有说服力,但遇到某些情况时就无能为力了。
于自己而言,我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来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不受外界影响,也因此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最小的伤害。
当然,任何好事物的影响也变得最小,我因此而受益,也因此而失去。
过去的这些年里我已经很少有机会能见到她了,这令我颇为失落,归根结底,还是我离开的太久了。就像一幅拼图,拆解的时候轻而易举,可想重新拼回时就难得多。
朋友在电话里讲着关于过去关于现在,关于痛恨关于平静,我试图站在一种更高的角度去理解和评价,却反倒发现显得愚蠢。那一刻我明白,我的理论又一次失效了。
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幻想着电话那边的北京天气晴朗明媚,他就站在三月的春风中温暖而平和。
水管的水压似乎不太稳定,淋浴时大时小,水卡仍然以每秒两分的速度不紧不慢地扣着费。
此刻的我站在淋浴中,一股巨大的暖流正流过身体的每个角落,回头看了眼水卡。
一块五毛。
我想,这澡洗的也太久,是时候出去了。